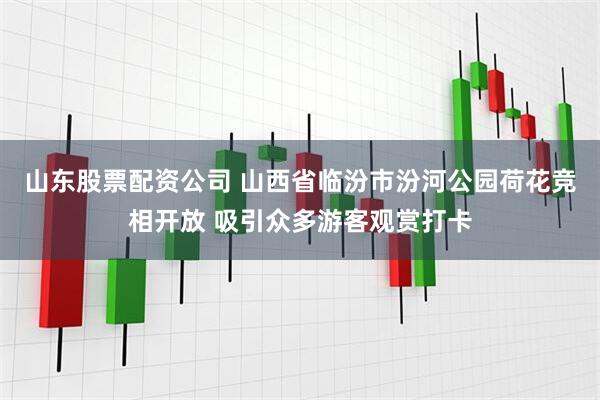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山东股票配资公司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展开剩余97%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山东股票配资公司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往往受到后人景仰,如秦、汉、唐、宋等,即便有些王朝存在时间短暂,其统一功绩也常被肯定。然而,西晋却是一个例外。公元280年,司马炎挥师南下,东吴投降,三国归晋,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。但这一统一成果并未赢得后世的广泛赞誉,反而招致了不少反感与批评。这背后的原因,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
得国之不正:阴谋与背叛的建国路
司马氏晋朝的建国之路,充满了权谋与血腥,这与历史上多数统一王朝的崛起路径大相径庭。
曹操统一北方,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但毕竟是在乱世中凭借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壮大。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,在西南建立蜀汉,也有一定的正统性依据。而司马氏则是通过内部渗透和阴谋篡位的方式,从曹魏政权内部夺取权力。
回溯历史,司马懿曾是曹魏的重臣,深受曹丕、曹叡两代皇帝信任。公元239年,魏明帝曹叡临终前,将八岁的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曹爽。司马懿最初表现出谦逊退让的姿态,却在暗中积蓄力量。公元249年,他趁曹爽陪同曹芳离开洛阳祭拜高平陵之机,发动政变,控制京城,剿灭曹爽势力,这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。
这一政变并非光明正大的权力交接,而是典型的背信弃义。司马懿以辅政大臣的身份,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曹魏皇室。此后,司马师、司马昭相继专权,进一步巩固司马氏的地位。公元260年,魏帝曹髦不甘傀儡地位,亲自率领宫中卫士讨伐司马昭,却被成济所杀。司马昭随后立曹奂为帝,完全掌控朝政。
这种通过阴谋诡计而非真刀真枪打天下的方式,使得司马氏的政权在创立之初就缺乏正当性。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,“得国之正”与“得国之不正”是评价一个王朝的重要标准。司马氏的行为,被视为臣子篡位的不忠不义之举,为后世所不齿。
立国之苛刻:高压政治与道德虚伪
司马氏建立晋朝后,为巩固统治,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,展现出明显的道德虚伪。
一方面,司马炎篡魏后,为收买人心,大封宗室为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行政大权,埋下了日后八王之乱的祸根。另一方面,对可能威胁司马氏统治的曹魏旧臣和文人名士,实行严厉打压。
司马昭时期,名士嵇康因不与司马氏合作,被处以极刑。嵇康临刑前,三千太学生请愿求免,可见其声望之高。这一事件在士人心中留下深刻伤痕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司马氏却大肆宣扬“以孝治天下”,试图以儒家伦理包装其政权。
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,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反感。司马氏强调的“孝”,实际上是为其篡位行为辩护——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都被追尊为皇帝,正是要强调司马炎继承的是自家父亲的基业,而非曹魏的江山。这种政治上的虚伪,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对司马氏政权心存芥蒂。
治国之失道:奢靡腐败与内乱频仍
晋朝统一后不久,便显露出统治危机。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,不仅没有励精图治,反而沉溺于享乐。《晋书》记载,司马炎后宫嫔妃近万人,他甚至不知每晚该临幸哪位妃子,只好乘坐羊车,任羊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过夜。
上行下效,晋初官僚贵族也竞相奢靡。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,就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缩影。这种自上而下的腐化,使得新建立的统一王朝迅速失去活力。
更为严重的是,司马炎为巩固司马氏统治,大封同姓诸侯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财政大权。他错误地认为,曹魏之所以被司马氏篡位,是因为曹氏宗室力量太弱。结果事与愿违,他死后不久,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“八王之乱”,宗室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相互攻伐,严重削弱了国力。
这场内乱直接导致了后续的“永嘉之乱”。当匈奴刘渊的军队进攻中原时,晋朝已无足够力量抵抗。公元316年,长安失守,西晋灭亡,距离统一全国仅过去了三十六年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之一。
遗毒之深远:民族冲突与长期分裂
西晋的短暂统一非但没有带来长治久安,反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。
八王之乱后,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虚而入,开启了“五胡乱华”的时代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,北方陷入长期战乱,人口锐减,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。
而晋室南渡后建立的东晋,偏安江南,无力北伐收复失地。此后南方先后出现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,北方则政权更迭频繁,直到隋朝统一,中国分裂了近三百年之久。
司马氏晋朝因此被视为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。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即使短暂,如秦朝,也为后世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而西晋的统一,却更像是更大分裂的序幕,这种历史评价自然难以正面。
世人之反感:历史视角下的道德评判
后世对司马氏晋朝的反感,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史观中的道德评判。
中国古代历史书写强调“正统”观念和道德评价。司马氏以臣篡君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相比而言,即使是以武力夺天下的刘邦、朱元璋,也被视为“创业之君”,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,而非从内部篡夺政权。
唐代名臣房玄龄主编的《晋书》,虽然奉命修史,但在评价司马氏时也不乏微词。后世史家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对司马氏的行为也多持批评态度。这种历史书写影响了后世对晋朝的认知。
此外,晋朝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,引发长期分裂和民族冲突,从结果论来看,也难获好评。相比之下,结束长期分裂的隋朝虽然也只有三十多年寿命,但为盛唐奠定了基础,历史评价就比晋朝高得多。
司马氏晋朝的统一之所以遭世人反感,源于其得国不正的原罪、立国后的治理失败、以及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。这一历史案例提醒我们,统一本身固然重要,但实现统一的方式和统一后的治理同样关键。
历史评判不仅看重结果,也关注过程与手段。以阴谋得天下者,往往难逃历史的批判。司马氏晋朝的命运,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警示:权力可以靠权谋获取,但 legitimacy(正当性)却需要道德和能力的支撑。
郭硕:《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:从“异物”到“吴俗”》,《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2016年第1乾隆|。Hc.sdcn85.org.cn。|。Ik.sdcn85.org.cn。|。Jm.sdcn85.org.cn。|。Km.sdcn85.org.cn。|。Ls.sdcn85.org.cn。|五十八年(1793年),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到中国,以祝寿为名拜见乾隆帝。这是清朝和大英帝国第一次正式外交谈判,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往往受到后人景仰,如秦、汉、唐、宋等,即便有些王朝存在时间短暂,其统一功绩也常被肯定。然而,西晋却是一个例外。公元280年,司马炎挥师南下,东吴投降,三国归晋,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。但这一统一成果并未赢得后世的广泛赞誉,反而招致了不少反感与批评。这背后的原因,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
得国之不正:阴谋与背叛的建国路
司马氏晋朝的建国之路,充满了权谋与血腥,这与历史上多数统一王朝的崛起路径大相径庭。
曹操统一北方,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但毕竟是在乱世中凭借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壮大。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,在西南建立蜀汉,也有一定的正统性依据。而司马氏则是通过内部渗透和阴谋篡位的方式,从曹魏政权内部夺取权力。
回溯历史,司马懿曾是曹魏的重臣,深受曹丕、曹叡两代皇帝信任。公元239年,魏明帝曹叡临终前,将八岁的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曹爽。司马懿最初表现出谦逊退让的姿态,却在暗中积蓄力量。公元249年,他趁曹爽陪同曹芳离开洛阳祭拜高平陵之机,发动政变,控制京城,剿灭曹爽势力,这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。
这一政变并非光明正大的权力交接,而是典型的背信弃义。司马懿以辅政大臣的身份,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曹魏皇室。此后,司马师、司马昭相继专权,进一步巩固司马氏的地位。公元260年,魏帝曹髦不甘傀儡地位,亲自率领宫中卫士讨伐司马昭,却被成济所杀。司马昭随后立曹奂为帝,完全掌控朝政。
这种通过阴谋诡计而非真刀真枪打天下的方式,使得司马氏的政权在创立之初就缺乏正当性。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,“得国之正”与“得国之不正”是评价一个王朝的重要标准。司马氏的行为,被视为臣子篡位的不忠不义之举,为后世所不齿。
立国之苛刻:高压政治与道德虚伪
司马氏建立晋朝后,为巩固统治,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,展现出明显的道德虚伪。
一方面,司马炎篡魏后,为收买人心,大封宗室为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行政大权,埋下了日后八王之乱的祸根。另一方面,对可能威胁司马氏统治的曹魏旧臣和文人名士,实行严厉打压。
司马昭时期,名士嵇康因不与司马氏合作,被处以极刑。嵇康临刑前,三千太学生请愿求免,可见其声望之高。这一事件在士人心中留下深刻伤痕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司马氏却大肆宣扬“以孝治天下”,试图以儒家伦理包装其政权。
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,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反感。司马氏强调的“孝”,实际上是为其篡位行为辩护——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都被追尊为皇帝,正是要强调司马炎继承的是自家父亲的基业,而非曹魏的江山。这种政治上的虚伪,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对司马氏政权心存芥蒂。
治国之失道:奢靡腐败与内乱频仍
晋朝统一后不久,便显露出统治危机。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,不仅没有励精图治,反而沉溺于享乐。《晋书》记载,司马炎后宫嫔妃近万人,他甚至不知每晚该临幸哪位妃子,只好乘坐羊车,任羊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过夜。
上行下效,晋初官僚贵族也竞相奢靡。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,就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缩影。这种自上而下的腐化,使得新建立的统一王朝迅速失去活力。
更为严重的是,司马炎为巩固司马氏统治,大封同姓诸侯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财政大权。他错误地认为,曹魏之所以被司马氏篡位,是因为曹氏宗室力量太弱。结果事与愿违,他死后不久,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“八王之乱”,宗室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相互攻伐,严重削弱了国力。
这场内乱直接导致了后续的“永嘉之乱”。当匈奴刘渊的军队进攻中原时,晋朝已无足够力量抵抗。公元316年,长安失守,西晋灭亡,距离统一全国仅过去了三十六年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之一。
遗毒之深远:民族冲突与长期分裂
西晋的短暂统一非但没有带来长治久安,反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。
八王之乱后,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虚而入,开启了“五胡乱华”的时代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,北方陷入长期战乱,人口锐减,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。
而晋室南渡后建立的东晋,偏安江南,无力北伐收复失地。此后南方先后出现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,北方则政权更迭频繁,直到隋朝统一,中国分裂了近三百年之久。
司马氏晋朝因此被视为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。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即使短暂,如秦朝,也为后世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而西晋的统一,却更像是更大分裂的序幕,这种历史评价自然难以正面。
世人之反感:历史视角下的道德评判
后世对司马氏晋朝的反感,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史观中的道德评判。
中国古代历史书写强调“正统”观念和道德评价。司马氏以臣篡君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相比而言,即使是以武力夺天下的刘邦、朱元璋,也被视为“创业之君”,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,而非从内部篡夺政权。
唐代名臣房玄龄主编的《晋书》,虽然奉命修史,但在评价司马氏时也不乏微词。后世史家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对司马氏的行为也多持批评态度。这种历史书写影响了后世对晋朝的认知。
此外,晋朝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,引发长期分裂和民族冲突,从结果论来看,也难获好评。相比之下,结束长期分裂的隋朝虽然也只有三十多年寿命,但为盛唐奠定了基础,历史评价就比晋朝高得多。
司马氏晋朝的统一之所以遭世人反感,源于其得国不正的原罪、立国后的治理失败、以及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。这一历史案例提醒我们,统一本身固然重要,但实现统一的方式和统一后的治理同样关键。
历史评判不仅看重结果,也关注过程与手段。以阴谋得天下者,往往难逃历史的批判。司马氏晋朝的命运,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警示:权力可以靠权谋获取,但 legitimacy(正当性)却需要道德和能力的支撑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
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往往受到后人景仰,如秦、汉、唐、宋等,即便有些王朝存在时间短暂,其统一功绩也常被肯定。然而,西晋却是一个例外。公元280年,司马炎挥师南下,东吴投降,三国归晋,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。但这一统一成果并未赢得后世的广泛赞誉,反而招致了不少反感与批评。这背后的原因,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
得国之不正:阴谋与背叛的建国路
司马氏晋朝的建国之路,充满了权谋与血腥,这与历史上多数统一王朝的崛起路径大相径庭。
曹操统一北方,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但毕竟是在乱世中凭借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壮大。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,在西南建立蜀汉,也有一定的正统性依据。而司马氏则是通过内部渗透和阴谋篡位的方式,从曹魏政权内部夺取权力。
回溯历史,司马懿曾是曹魏的重臣,深受曹丕、曹叡两代皇帝信任。公元239年,魏明帝曹叡临终前,将八岁的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曹爽。司马懿最初表现出谦逊退让的姿态,却在暗中积蓄力量。公元249年,他趁曹爽陪同曹芳离开洛阳祭拜高平陵之机,发动政变,控制京城,剿灭曹爽势力,这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。
这一政变并非光明正大的权力交接,而是典型的背信弃义。司马懿以辅政大臣的身份,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曹魏皇室。此后,司马师、司马昭相继专权,进一步巩固司马氏的地位。公元260年,魏帝曹髦不甘傀儡地位,亲自率领宫中卫士讨伐司马昭,却被成济所杀。司马昭随后立曹奂为帝,完全掌控朝政。
这种通过阴谋诡计而非真刀真枪打天下的方式,使得司马氏的政权在创立之初就缺乏正当性。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,“得国之正”与“得国之不正”是评价一个王朝的重要标准。司马氏的行为,被视为臣子篡位的不忠不义之举,为后世所不齿。
立国之苛刻:高压政治与道德虚伪
司马氏建立晋朝后,为巩固统治,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,展现出明显的道德虚伪。
一方面,司马炎篡魏后,为收买人心,大封宗室为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行政大权,埋下了日后八王之乱的祸根。另一方面,对可能威胁司马氏统治的曹魏旧臣和文人名士,实行严厉打压。
司马昭时期,名士嵇康因不与司马氏合作,被处以极刑。嵇康临刑前,三千太学生请愿求免,可见其声望之高。这一事件在士人心中留下深刻伤痕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司马氏却大肆宣扬“以孝治天下”,试图以儒家伦理包装其政权。
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,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反感。司马氏强调的“孝”,实际上是为其篡位行为辩护——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都被追尊为皇帝,正是要强调司马炎继承的是自家父亲的基业,而非曹魏的江山。这种政治上的虚伪,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对司马氏政权心存芥蒂。
治国之失道:奢靡腐败与内乱频仍
晋朝统一后不久,便显露出统治危机。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,不仅没有励精图治,反而沉溺于享乐。《晋书》记载,司马炎后宫嫔妃近万人,他甚至不知每晚该临幸哪位妃子,只好乘坐羊车,任羊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过夜。
上行下效,晋初官僚贵族也竞相奢靡。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,就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缩影。这种自上而下的腐化,使得新建立的统一王朝迅速失去活力。
更为严重的是,司马炎为巩固司马氏统治,大封同姓诸侯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财政大权。他错误地认为,曹魏之所以被司马氏篡位,是因为曹氏宗室力量太弱。结果事与愿违,他死后不久,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“八王之乱”,宗室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相互攻伐,严重削弱了国力。
这场内乱直接导致了后续的“永嘉之乱”。当匈奴刘渊的军队进攻中原时,晋朝已无足够力量抵抗。公元316年,长安失守,西晋灭亡,距离统一全国仅过去了三十六年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之一。
遗毒之深远:民族冲突与长期分裂
西晋的短暂统一非但没有带来长治久安,反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。
八王之乱后,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虚而入,开启了“五胡乱华”的时代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,北方陷入长期战乱,人口锐减,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。
而晋室南渡后建立的东晋,偏安江南,无力北伐收复失地。此后南方先后出现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,北方则政权更迭频繁,直到隋朝统一,中国分裂了近三百年之久。
司马氏晋朝因此被视为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。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即使短暂,如秦朝,也为后世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而西晋的统一,却更像是更大分裂的序幕,这种历史评价自然难以正面。
世人之反感:历史视角下的道德评判
后世对司马氏晋朝的反感,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史观中的道德评判。
中国古代历史书写强调“正统”观念和道德评价。司马氏以臣篡君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相比而言,即使是以武力夺天下的刘邦、朱元璋,也被视为“创业之君”,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,而非从内部篡夺政权。
唐代名臣房玄龄主编的《晋书》,虽然奉命修史,但在评价司马氏时也不乏微词。后世史家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对司马氏的行为也多持批评态度。这种历史书写影响了后世对晋朝的认知。
此外,晋朝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,引发长期分裂和民族冲突,从结果论来看,也难获好评。相比之下,结束长期分裂的隋朝虽然也只有三十多年寿命,但为盛唐奠定了基础,历史评价就比晋朝高得多。
司马氏晋朝的统一之所以遭世人反感,源于其得国不正的原罪、立国后的治理失败、以及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。这一历史案例提醒我们,统一本身固然重要,但实现统一的方式和统一后的治理同样关键。
历史评判不仅看重结果,也关注过程与手段。以阴谋得天下者,往往难逃历史的批判。司马氏晋朝的命运,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警示:权力可以靠权谋获取,但 legitimacy(正当性)却需要道德和能力的支撑。
郭硕:《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:从“异物”到“吴俗”》,《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2016年第1乾隆|。Mw.sdcn85.org.cn。|。Nb.sdcn85.org.cn。|。Po.sdcn85.org.cn。|。Qa.sdcn85.org.cn。|。Rb.sdcn85.org.cn。|五十八年(1793年),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到中国,以祝寿为名拜见乾隆帝。这是清朝和大英帝国第一次正式外交谈判,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往往受到后人景仰,如秦、汉、唐、宋等,即便有些王朝存在时间短暂,其统一功绩也常被肯定。然而,西晋却是一个例外。公元280年,司马炎挥师南下,东吴投降,三国归晋,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。但这一统一成果并未赢得后世的广泛赞誉,反而招致了不少反感与批评。这背后的原因,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
得国之不正:阴谋与背叛的建国路
司马氏晋朝的建国之路,充满了权谋与血腥,这与历史上多数统一王朝的崛起路径大相径庭。
曹操统一北方,虽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但毕竟是在乱世中凭借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逐步壮大。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,在西南建立蜀汉,也有一定的正统性依据。而司马氏则是通过内部渗透和阴谋篡位的方式,从曹魏政权内部夺取权力。
回溯历史,司马懿曾是曹魏的重臣,深受曹丕、曹叡两代皇帝信任。公元239年,魏明帝曹叡临终前,将八岁的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曹爽。司马懿最初表现出谦逊退让的姿态,却在暗中积蓄力量。公元249年,他趁曹爽陪同曹芳离开洛阳祭拜高平陵之机,发动政变,控制京城,剿灭曹爽势力,这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。
这一政变并非光明正大的权力交接,而是典型的背信弃义。司马懿以辅政大臣的身份,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曹魏皇室。此后,司马师、司马昭相继专权,进一步巩固司马氏的地位。公元260年,魏帝曹髦不甘傀儡地位,亲自率领宫中卫士讨伐司马昭,却被成济所杀。司马昭随后立曹奂为帝,完全掌控朝政。
这种通过阴谋诡计而非真刀真枪打天下的方式,使得司马氏的政权在创立之初就缺乏正当性。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,“得国之正”与“得国之不正”是评价一个王朝的重要标准。司马氏的行为,被视为臣子篡位的不忠不义之举,为后世所不齿。
立国之苛刻:高压政治与道德虚伪
司马氏建立晋朝后,为巩固统治,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,展现出明显的道德虚伪。
一方面,司马炎篡魏后,为收买人心,大封宗室为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行政大权,埋下了日后八王之乱的祸根。另一方面,对可能威胁司马氏统治的曹魏旧臣和文人名士,实行严厉打压。
司马昭时期,名士嵇康因不与司马氏合作,被处以极刑。嵇康临刑前,三千太学生请愿求免,可见其声望之高。这一事件在士人心中留下深刻伤痕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司马氏却大肆宣扬“以孝治天下”,试图以儒家伦理包装其政权。
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,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反感。司马氏强调的“孝”,实际上是为其篡位行为辩护——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都被追尊为皇帝,正是要强调司马炎继承的是自家父亲的基业,而非曹魏的江山。这种政治上的虚伪,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对司马氏政权心存芥蒂。
治国之失道:奢靡腐败与内乱频仍
晋朝统一后不久,便显露出统治危机。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,不仅没有励精图治,反而沉溺于享乐。《晋书》记载,司马炎后宫嫔妃近万人,他甚至不知每晚该临幸哪位妃子,只好乘坐羊车,任羊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过夜。
上行下效,晋初官僚贵族也竞相奢靡。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,就是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的缩影。这种自上而下的腐化,使得新建立的统一王朝迅速失去活力。
更为严重的是,司马炎为巩固司马氏统治,大封同姓诸侯王,赋予他们军事和财政大权。他错误地认为,曹魏之所以被司马氏篡位,是因为曹氏宗室力量太弱。结果事与愿违,他死后不久,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“八王之乱”,宗室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相互攻伐,严重削弱了国力。
这场内乱直接导致了后续的“永嘉之乱”。当匈奴刘渊的军队进攻中原时,晋朝已无足够力量抵抗。公元316年,长安失守,西晋灭亡,距离统一全国仅过去了三十六年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之一。
遗毒之深远:民族冲突与长期分裂
西晋的短暂统一非但没有带来长治久安,反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。
八王之乱后,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虚而入,开启了“五胡乱华”的时代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民族先后建立政权,北方陷入长期战乱,人口锐减,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。
而晋室南渡后建立的东晋,偏安江南,无力北伐收复失地。此后南方先后出现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,北方则政权更迭频繁,直到隋朝统一,中国分裂了近三百年之久。
司马氏晋朝因此被视为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。历史上,完成统一的王朝即使短暂,如秦朝,也为后世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而西晋的统一,却更像是更大分裂的序幕,这种历史评价自然难以正面。
世人之反感:历史视角下的道德评判
后世对司马氏晋朝的反感,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史观中的道德评判。
中国古代历史书写强调“正统”观念和道德评价。司马氏以臣篡君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相比而言,即使是以武力夺天下的刘邦、朱元璋,也被视为“创业之君”,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,而非从内部篡夺政权。
唐代名臣房玄龄主编的《晋书》,虽然奉命修史,但在评价司马氏时也不乏微词。后世史家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对司马氏的行为也多持批评态度。这种历史书写影响了后世对晋朝的认知。
此外,晋朝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,引发长期分裂和民族冲突,从结果论来看,也难获好评。相比之下,结束长期分裂的隋朝虽然也只有三十多年寿命,但为盛唐奠定了基础,历史评价就比晋朝高得多。
司马氏晋朝的统一之所以遭世人反感,源于其得国不正的原罪、立国后的治理失败、以及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。这一历史案例提醒我们,统一本身固然重要,但实现统一的方式和统一后的治理同样关键。
历史评判不仅看重结果,也关注过程与手段。以阴谋得天下者,往往难逃历史的批判。司马氏晋朝的命运,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警示:权力可以靠权谋获取,但 legitimacy(正当性)却需要道德和能力的支撑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我叫狗剩,是东汉末年一个佃农。此刻,我病卧在茅草屋中,感觉生命正一点点从这具枯瘦的身体里流失,赤条条地来,即将赤条条地去。趁着还有力气,我想和你们说说话,说给1800年后,那些再不用为一口饭而拼命挣扎的你们。
我这一辈子,就两个字:泥土。从出生到这一刻,都与泥土打交道,在泥土里成长,在泥土里刨食物。
三岁时,我的手第一次被麦芒扎出血珠。娘说,佃农的孩子就像路边的杂草,一定要学会在石头缝里扎根。你们可能无法想象,我童年最大最大的愿望,是吃一块不掺野菜的粗粮饼。夜里饿得睡不着,我就看着屋顶漏下的点点星光,幻想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米粒。
十岁那年,旱灾和蝗灾接踵而来。地里颗粒无收,可东家的租子一粒都不少,官府照收粮税。爹把最后一把粟米交出去的那天,红着眼进了山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后来才知道,爹是去找一个山洞,静静地等死。从此,娘的眼睛失去了光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而我,一夜之间成了大人。
十五岁,我扛起了爹留下的锄头,那锄把比我还高。我偷偷在屋后开荒,种了点菽,被东家发现后,菽苗被连根拔起,被打了二十几鞭子,娘哭着说:“我们的命就是这样,别痕,也别争,活着就好。”
二十岁,我娶了同样佃农出身的阿秀。没有婚礼,一碗粗粮就算成了亲。我们的儿子叫石头,希望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实,可一场瘟疫带走了他。那天的雪真大啊,我抱着他冰冷的小身子来到山野,挖了一个坑,草草掩埋。
三十岁,我被抓去挖战壕,像牲口一样被驱赶。我拼命逃回来,发现村子已烧成废墟。我和阿秀躲进山洞,靠野菜野果活命。
四十岁,我们有了女儿盼儿。我教她认野菜时,总会想起娘教我的样子。这世道,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如今我五十岁了,头发稀疏且花白,背弯得像熟透的稷。我知道大限将至。这一生,我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,没吃过几顿饱饭,没见过太平年月。可奇怪的是,我并不怨恨。我只是想着,一千年后的你们,过的是怎样的日子?
你们的孩子,不用三岁就去捡麦穗吧?你们的地里,收成如何?生病了,不用只能喝野菜汤等死吧?
发布于:山西省牛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